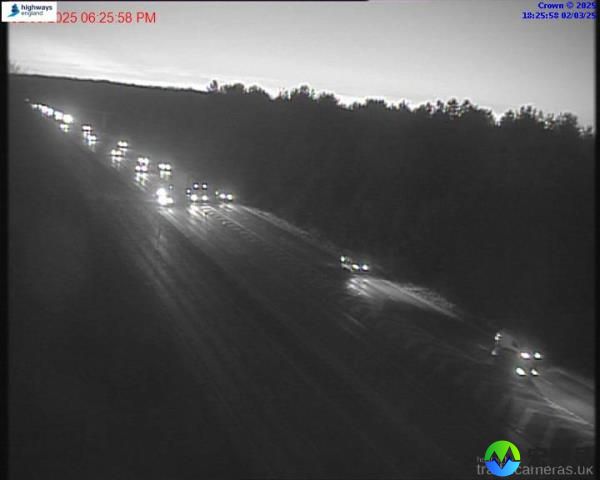它开始于当天的最后一堂地理课:我们正在复习冰川是如何形成的,在关于压缩迫使雪重新结晶成冰的部分。
我还记得教室高高的天花板和巨大的维多利亚式窗扇,以及外面一月份的阳光迅速消失的样子。
我们没有坐在书桌前。桌子被安排在一个大广场上,我们这群参加a -level考试的一年级新生围坐在桌子边上,一边埋头读着课本,一边已经在为晚上的事情做准备了——坐公交车回家,吃晚饭,找朋友。
然后我感到一只脚碰到了我的脚。那不是轻拂,而是明确的轻推。它继续在桌子底下推着,绕着我的脚转,很坚决,看不见。
为好奇的澳大利亚人提供**、商业、文化和观点方面的新闻。
读到现在
我抬起头来,很困惑。
我没有男朋友,据我所知,也没有任何爱慕我的人愿意在地理课上偷偷摸摸地跟我玩**。
所有的男孩都在低头看他们的书。但这时,我们的老师——我们叫他的名字,詹姆斯(显然不是他的真名)——抬起头,对我笑了笑,笑得那么会心,让人看不出那只脚是他的。
37年后,我仍然回想起那一刻,那股红晕从我的脖子爬到我的脸上,那是青春期的悸动。
我仍然想知道,是什么让他,一个30多岁的已婚男人,在几个月后,和一个从未有过男朋友、还是处男的女孩走下悬崖。
这一幕肯定在数百间教室和私人辅导课上上演过。
我当时不知道这是什么陈词滥调——实际上对任何事情都不太了解。
我从萨默塞特的一所女子修道院进入了这所六年级学院,我在那里寄宿了八年。
说我被庇护是一种轻描淡写的说法。因此,尽管有些人可能会认为这太过分了,但我还是支持剑桥大学(Cambridge University)打击师生关系的决定。
从7月1日起生效的新规定将禁止学生和教授发生性行为,如果导师对相关学生负有“任何直接或间接的学术责任”。
学生们还将被警告不要与教职员调情。
如果在我上六年级的时候有类似的事情发生,我的老师可能就不会占我的便宜了。
当时我并没有这样的感觉——我太天真了,把我们的恋情看作是一次冒险,是我第一次尝到成人生活的滋味。
直到现在我才知道它造成了多大的伤害。16岁时,我并不是一个早熟的诱惑者,散发着性感和自信。
如果说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我笨手笨脚,长相有点怪,有点布卢姆斯伯里派的风格——圆框金属框眼镜(我不需要),长裙,粗花呢夹克。
但我很有趣。我是无可救药的浪漫在一种荒谬的,什么都愿意做的方式。
所以,从我第一次见到詹姆斯的那一刻起,我就完全被他迷住了。
他不仅是我的A-level地理老师,也是我的私人导师。
入学那天,当我找到我的教室时,他一个人在里面,在椅子上晃来晃去,脚搭在桌子上。
我看了看他的细绳裤、棕色粗革鞋和略微蓬乱的头发。我在修院里唯一接触过的异性是肯尼迪神父,我们都偷偷喜欢他。(不要评头论足——地面上的男人很瘦)。
詹姆斯上下打量了我一番,咧嘴一笑,说:“有人付钱让你穿那套衣服吗?”
一开始我对他毫无希望的迷恋,很快就变成了一种无法抗拒的痴迷,而他却没有阻止我。
我的父母正在经历一场混乱的离婚,所以在家里,没有人注意到我在做什么。
大学毕业后,我很容易留下来帮忙整理地理教室,或者——更可悲的是——在学院的走廊里徘徊,希望他能停下来和我说话。
詹姆斯把写诗作为一种爱好,在其他老师都走了很久之后,他开始让我在教工室的电脑上帮他打字。
他没有靠近我,老实说,我也不相信他会靠近我。但这并没有阻止我对他的崇拜,当我成年后回头看时,我可以看出这对他来说一定是显而易见的。
作为三个年轻女孩的母亲,我花了几个小时试图弄清楚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几十年来,我一直告诉自己,我无耻地追求这个男人,在大学里跟踪他,在停车场等着看他离开的一瞥。
我为发生的事情责怪自己,好像我才是那个掠夺者,追求我已婚的老师,直到他再也无法抗拒。
我很尴尬地承认,我的三个二十多岁的孩子迫使我明白,这种精心制作的叙述完全是胡说八道。
当我回忆起我的师生恋情,并把它描述为某种塑造性格的、令人遗憾的冒险时,他们同情地看着我。
“妈妈,你是精心打扮的,”他们说,带着Z世代所擅长的那种坚定不移的正义感。
即便如此,我还是对被归入受害者的行列感到不舒服。我喜欢认为我能控制事情的发展。
我也非常想要它。为了表扬詹姆斯,除了他丢给我的那些卑微的工作,就像给一只渴望的小狗喂肉汁骨头一样,他在第一年对我的抵制相当负责。
事情发展得非常缓慢,我现在可以仔细观察了。
17岁那年,我开始了第二年的a -level考试。我离开教室时,他的手放在我的后腰上,他的脚在桌下碰了碰我的脚。还有很多玩笑。
他不断地侮辱我的穿着、我的写作和我对地理的理解,“天哪,肖娜,你就不能做得更好吗?”他会厉声说,这句话反而让我更晕了。
第二年的圣诞节临近时,我的情绪开始崩溃。对任何注意到我的人来说,很明显我有一种无法控制的——而且是不恰当的——痴迷。
詹姆斯在地理系的一位同事甚至把我拉到一边,同情地建议我和别人谈谈我的感受。
相反,在一个勇敢而鲁莽的举动中,我决定是时候向詹姆斯本人表白了。
我在他的办公室外站了一个小时,才鼓起勇气敲门,向他表达我强烈的感情。
我不知道他会作何反应,但我不在乎。我只是想让他知道。接下来发生的事将永远铭刻在我的脑海里。
他没有警告我,也没有善意地建议我如何正确处理师生关系。
相反,他小心翼翼地绕着桌子走了一圈,双臂环抱着我说:“我知道你的感受。但告诉别人可能不是个好主意。”
就这样,底线被越过了。任何一个理智的成年人从外部世界来看,都会看到这是一种权力滥用。我刚刚看到一个任务完成了。
几天后,我们在他的车里接吻了。
第一次**发生在员工室的一张旧切斯特菲尔德沙发上,当时其他人都回家了。
我记得后来他开车送我回家,左手放在我膝盖上,手指上戴着结婚戒指。
当我们到达我家时,母亲请他进屋,给了他一杯酒,然后开始问我的功课怎么样了。
不过,我觉得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我觉得——愚蠢地——那是爱。与一个身居高位的人发生这种被禁止的关系,让我兴奋不已。
这是《米尔斯与布恩》(Mills & Boon)的素材,是每个少女的幻想情节。
但实际上,这根本不是一种“合适的”关系。
我们从未做过大学以外的事。我们之间的联系——这是我每天都希望的——包括在教室里没人看的时候匆匆一吻,或者在我离开课堂时迅速捏一下我的屁股——我总是最后一个离开,直到最后一刻才离开,等待他扔给我的任何身体接触。
偶尔,詹姆斯会开车送我回家,我们会在厨房的地毯上**。
我们从来没有冒险进入卧室,因为害怕被抓住,而性本身——我现在知道——完全不能令人满意。
它总是在一秒钟内结束,让我想知道所有的大惊小怪的是什么。
回想起来,这听起来很疯狂,但我也从未使用过避孕措施。整件事感觉太不真实了,我在一片茫然中经历着我们的恋情。
我知道我完全不知所措了。我本应该和詹姆斯谈谈我们在做什么,但我从来没有。他对我来说是如此的崇拜,以至于我不知道如何在那种程度上与他交谈。
我记得我不敢让他解释我们在做什么,因为我怕他会被吓到。我几乎感觉自己在屏住呼吸,不做任何突然的动作,以免把他吓跑。
我现在明白了,他不跟我谈这件事,可能是为了假装这件事根本没发生过。夏季学期临近结束时,詹姆斯毫不客气地退出了。
我永远不会忘记在学期的最后一天站在院子里,看着他离开,他的皮书包摇摆着。我抖得厉害,好不容易才没倒在地上。
我所期望的是什么?谁知道呢?如果不是一起走到夕阳下,至少不会像不想要的衣服一样被丢弃。友善的东西。
我曾愚蠢地以为他也有同样的感觉,而我从来没有处于平等的地位去问他。我完全没有准备好这会给我带来怎样的冲击。在去上大学之前,我整个暑假都假装没事。
我花了好几年的时间来处理情感上的损失,并明白用不恰当的师生关系来衡量每一段未来的关系并不是成功爱情生活的最佳配方。
我有一个14岁的女儿,很快就要参加a -level考试了,当我想象同样的事情发生时,我感到非常不安。
我终于看到了事情的本来面貌:一个情绪不成熟的少年和一个软弱的老人,他可能会(也可能不会)继续对其他女学生做出这种不恰当的行为。
他现在退休了,事业辉煌,在教育界步步高升。他冒着一切风险。为了什么?可悲的是,我还是不确定我是否值得这么做。